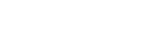《暗恋桃花源话剧观后感【优秀4篇】》
《暗恋》就像是一个将醒未醒的梦,而《桃花源》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与《暗恋》那种安静伤感的氛围不一样,《桃花源》却是极富感染力的喜剧。这里是细心的小编帮大家收集整理的暗恋桃花源话剧观后感【优秀4篇】,仅供借鉴。
暗恋桃花源观后感 篇1
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被《洛杉矶时报》称为“台湾剧场最明亮的灯”,而他的《暗恋桃花源》也做为其代表作被对台湾话剧有兴趣的观众所注意,而对于该剧所表现的主题历来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由于该剧有话剧和电影两个不同的版本,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根据话剧《暗恋桃花源》所改编的电影。
先看《暗恋桃花源》的主要剧情,应该说,《暗恋桃花源》是借由两个三流剧组《暗恋》和《桃花源》在公演前一天抢夺剧场开始彩排而展开剧情的。其中《暗恋》是讲一对乱世爱侣江滨柳与云之凡相爱又不能相守的悲剧,《桃花源》则以渔夫老陶(桃)、春花(花)夫妇,与袁(源)老板之间错综的三角关系为经纬编织桃源和武陵的落差。表面上看,这两部话剧一部是庸俗小资情调的怀旧戏,一部是民间曹台班子的闹剧,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反对去把《暗恋桃花源》的具体情节做任何过渡诠释。我们认为,《暗恋桃花源》的第一个意义在于他的结构上而并非内容上。
自有剧场演出以来,人们普遍形成了艺术高于生活的共识,在审美的定义下,艺术和生活的空间越来越被人为的分割,直到自然主义提出的“第四面墙”理论为极至。这种分割固然可以保证剧场演出的严密性,但也限制了剧场空间的扩展,观众在剧场中完全成为了客体,失去了主动参与戏剧的可能,也使戏剧被禁锢在简单的“虚构”和“真实”之上而不能自拔。大多数话剧观众对话剧的欣赏仅仅停留在“像”与“不像”的阶段上。而随着现代声光技术的发达,剧场中的 “像”与“不像”显然已经毫无意义,这个时候,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打破这“第四面墙”,如何在空间上造成融合了。
在《暗恋桃花源》中,导演使用了套层结构,即戏中戏的形式。整个电影在一个大故事(两剧团争剧场)的故事之下又有两个话剧的演出。我们注意到,《暗恋桃花源》讲的是“现在”。对全片来说,电影时空几乎是和现实时空同步的;“暗恋”讲的是“过去”,是戏中戏之一,它的舞台时间主导了影片的电影时间;“桃花源”讲的是“遥远”,是戏中戏之二,它的舞台时间主导了影片的电影时间;而当两剧组同在舞台上并发生冲突时,是戏本身,一个不断来寻找刘子骥的女人暗示了影片基本电影时间架构的现在时态。这种套层结构的使用很明显,就是让片中片/虚构中的虚构与影象叙事的另一部分/虚构中的真实形成两相对照的镜像文本,他们彼此折射、彼此包容与说明,以及另一互文本的方式构成同一文本叙事。也就是说,实际上两个话剧起了结构上互相支撑,文本上互相解读的功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坚持认为不能将其中任何一剧单独拿出来分解。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影片所讲述的是三个故事,而这三个故事的比例大概为2:4:4。根据剧情,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解读出来《暗恋》和《桃花源》的关系,即互相对照。桃花源中武陵即暗恋中做为凡人的江滨柳的生活,而桃花源则是江滨柳心中的云之凡。按照赖声川的说法,《桃花源》是补充说明《暗恋》的,也就是说,《桃花源》是《暗恋》的又一个结局,《桃花源》的最后袁老板和春花陷入无奈的生活中就是江滨柳和云之凡的又一结局。有人就此在这个层面上指出,《暗恋桃花源》讨论的是爱情和幸福的或然性和必然性。这当然是一种解读,但总还是太过表层,这种解读只解决了两个独立的文本之间的表层联系,没有很好的深入内部。
让我们注意一下做为话剧的《暗恋桃花源》的创作时间,《暗恋桃花源》的首演,是在1986年3月3日,熟悉台湾历史的人都知道,1986年是台湾的临界点,正是台湾戒严与解严交接的日子,此时的台湾正处于变化和不变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暗恋桃花源》的出现如果仅仅是对爱情和幸福的探讨,那也就不会如此的受关注。如果我们注意到江滨柳这个人物,就会发现,赖声川借此所做的是台湾历史和未来的思考。正如朱天文所说:赖声川的戏剧每次公演,都成为负有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的社交活动。而如果我们从文化的意义上考虑,则会发现,在两剧交替演出和台词的穿插的背后,两个戏剧即进行了相互诠释和影射,也做了相互的解构。
在《暗恋桃花源》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两种话语权的斗争,《暗恋》所代表的传统正剧话语受到了《桃花源》所代表的解构性话语的挑战,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话语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正如巴赫金所说:“自我“永远无法获得完全的自主性”,每一种话语都试图在与别种话语的交谈中“成为标准的、特权的话语”。而在《暗恋桃花源》中,这种话语的斗争直接体现为谁占据“舞台”,谁成为权威话语。甚至到了最后,导演干脆让两剧发生正面冲突:
“桃”导演:我好好一出喜剧,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的……
“暗”导演:好,老弟,你不说我还不好意思说,我看你的喜剧,我好痛心啊,我最崇拜陶渊明了。
“桃”导演:好好好,没有关系,你不讲我也不讲。我看你的悲剧我很想笑。
“暗”导演:什么话
“桃”导演:什么话?你自己看看,一个快要死的病人,从床上爬下来,嘴里哼着歌去荡秋千啊!这叫什么玩艺儿!啊?还有山茶花,山茶花怎么演?你现在演给我看,你演,你演!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清楚的获得了导演发送的信息,那就是,他所要讲述的,与其说是关于幸福的问题,不如说是更深远的关于文化的问题,由此我们说,《暗恋桃花源》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寓言。
让我们从电影的镜头和布景入手去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
在《暗恋》中,色彩暗淡沉重,顶光使用逐渐减少,侧光增加,给人凝重又真实的感觉。而当影片进入到《桃花源》时,色彩顿时转为明快夸张,多用绿,粉红,蓝色系,使用全光,少有补光,这种非写实性的光色设计和大量的正面长镜头突出了剧场感。而《桃花源》的布景则采用传统的山水画,这样的设计充分运用了中国文化传统符号,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意识,也是台湾外省移民心中的家园形象,是一个美好的“中国“形象”。但当观众发现这样和谐的布景上有一块完全的空白的时候,文化上的断裂感就以直观的形式出现了。在这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中国人共有的传统文化意向被割裂后造成的景观。凝滞而沉重的历史和虚幻的未来同时呈现在了观众面前,也就是接受美学所津津乐道的召唤结构。而在赖声川那里,这个裂痕也就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比和呼应,而这种呼应不但是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隐喻,也是历史和未来的隐喻,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暗恋桃花源》获得了更深远的意义。
暗恋桃花源观后感 篇2
看完台湾导演赖声川《暗恋桃花源》后,我无比的兴奋,虽然上了一夜的班,可丝毫感觉不到疲倦,尽兴之余,写点观后感,留个纪念。
两部话剧:一个古装的喜剧,一个现代的杯具;一个胡编乱造猥亵经典,一个追忆历史述说往事;一个追求搞笑虚情假意,一个重述真情情真意切。演员台上表现拙劣,台下语出惊人,两台毫不相关的话剧摆在同一舞台上竟然能串上台词到达令人叫绝的喜剧效果,透过比较其分别对“爱”的表述,竟让人产生哲理的思考。在此不由让人折服于作者的天才创作。这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方式给我眼前一亮,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化腐朽为神奇?
单从两个话剧来说,毫无新意。《暗恋》演的俗套,就是因为导演的“绝大多数的真实”而被搬上了舞台,可他的演员却怎样也演不出那种“像一朵美丽山茶花”的效果、“牵着小手”的那种感觉,对历史沧桑的感觉和对感情的真挚,是这代像小护士一样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出来、理解的了的,它只能残存在导演的心中。导演那份以前的感情只能在台下引来我们这些观众的同情。《桃花源》简直是颠覆传统的表现,显然是受了西方某种思想的影响,它以其夸张的语言和搞笑的表演形式,用古代的故事讲述现代生活,穿越古今,杂糅并取,一味造些笑料,剧中语言竟不如台下的对白,更何谈其思想。可就是这样的两部很粗糙的话剧,作者巧夺天工,把它们放在了一齐,再加上些许台下捣乱的人,用一个争戏台的冲突,完美地结合在一齐,起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而且他也颠覆了一种人的思维模式,不好的演技也演出好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在此略微说明一下。
这部剧很明显是一个剧中剧,在此稍加以说明以便表述。两个话剧我们把它 在“一剧”里,演员的演技是很普通的,可从“二剧”的立场来看,它又是那么地有意思。差有差的妙用,就是因为他们在“一剧”中的水平差才展现出了“二剧”中的喜剧效果。就这样“一剧”里的两部部水准不高的话剧演员透过争舞台这个矛盾,再加上舞台上捣乱的女子、关门的看管员、突然冲上台指导的导演和幕后工作者的滑稽,就这些人在舞台上乱七八糟的表现,共同构成“二剧”。这两个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构成了新鲜活泼的艺术效果。
还有一笔值得一提,就是这种剧中剧所产生的特殊效果。那种一会儿在《暗恋》中、一会儿又在《桃花源》中,一会儿又把人拉在剧中,让观众做剧中的观众。产生这种效果,的确是个意外的收获。
再看看“一剧”和“二剧”中的感情。虽说两个话剧不相干,但是它们分别表现了“感情”,简单地透过比较竟到达了哲学的高度。一个是热恋的爱人分手数十载,其爱越久迷香;一个是为爱媾和却又为生活所累,引发了人对感情与生活这个永久话题的再次思考。
整个剧以其平平淡淡的对话结束,这种手法确实是真爱的流露,展现“一剧”中导演的真情流露、同样也体现了“二剧”导演的高超指导水平。积淀了几十年的感情,积攒了几十年的话,情怎能续?话如何说?最后只能是用几句简单的问候草草结束。这种“留白”真的是给人留以无尽的遐想,“大爱无言”的感情、大巧若拙的手法着实高明,值得我们学习。
暗恋桃花源观后感 篇3
看完台湾导演赖声川《暗恋桃花源》后,我无比的兴奋,虽然上了一夜的班,可丝毫感觉不到疲倦,尽兴之余,写点观后感,留个纪念。
两部话剧:一个古装的喜剧,一个现代的悲剧;一个胡编乱造猥亵经典,一个追忆历史述说往事;一个追求搞笑虚情假意,一个重述真情情真意切。演员台上表现拙劣,台下语出惊人,两台毫不相关的话剧摆在同一舞台上竟然能串上台词达到令人叫绝的喜剧效果,通过对比其分别对“爱”的表述,竟让人产生哲理的思考。在此不由让人折服于作者的天才创作。这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方式给我眼前一亮,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化腐朽为神奇?
单从两个话剧来说,毫无新意。《暗恋》演的俗套,就是因为导演的“绝大多数的真实”而被搬上了舞台,可他的演员却怎么也演不出那种“像一朵美丽山茶花”的效果、“牵着小手”的那种感觉,对历史沧桑的感觉和对爱情的真挚,是这代像小护士一样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出来、理解的了的,它只能残存在导演的心中。导演那份曾经的感情只能在台下引来我们这些观众的同情。《桃花源》简直是颠覆传统的表现,显然是受了西方某种思想的影响,它以其夸张的语言和搞笑的表演形式,用古代的故事讲述现代生活,穿越古今,杂糅并取,一味造些笑料,剧中语言竟不如台下的对白,更何谈其思想。可就是这样的两部很粗糙的话剧,作者巧夺天工,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再加上些许台下捣乱的人,用一个争戏台的冲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起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而且他也颠覆了一种人的思维模式,不好的演技也演出好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在此略微说明一下。
这部剧很明显是一个剧中剧,在此稍加以说明以便表述。两个话剧我们把它 在“一剧”里,演员的演技是很普通的,可从“二剧”的立场来看,它又是那么地有意思。差有差的妙用,就是因为他们在“一剧”中的水平差才展现出了“二剧”中的喜剧效果。就这样“一剧”里的两部部水准不高的话剧演员通过争舞台这个矛盾,再加上舞台上捣乱的女子、关门的看管员、突然冲上台指导的导演和幕后工作者的滑稽,就这些人在舞台上乱七八糟的表现,共同构成“二剧”。这两个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了新鲜活泼的艺术效果。
还有一笔值得一提,就是这种剧中剧所产生的特殊效果。那种一会儿在《暗恋》中、一会儿又在《桃花源》中,一会儿又把人拉在剧中,让观众做剧中的观众。产生这种效果,的确是个意外的收获。
再看看“一剧”和“二剧”中的爱情。虽说两个话剧不相干,可是它们分别表现了“爱情”,简单地通过对比竟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一个是热恋的爱人分手数十载,其爱越久迷香;一个是为爱媾和却又为生活所累,引发了人对爱情与生活这个永久话题的再次思考。
整个剧以其平平淡淡的对话结束,这种手法确实是真爱的流露,展现“一剧”中导演的真情流露、同样也体现了“二剧”导演的高超指导水平。积淀了几十年的爱情,积攒了几十年的话,情怎能续?话如何说?最后只能是用几句简单的问候草草结束。这种“留白”真的是给人留以无尽的遐想,“大爱无言”的感情、大巧若拙的手法着实高明,值得我们学习。
暗恋桃花源观后感 篇4
一个舞台,两个剧组。说是一场闹剧,或是一次深深的感动。
身穿白色旗袍的云之凡坐在秋千上,缓缓说着全剧第一句台词:“好安静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声音在响起的那一瞬间,突然觉得舞台好空旷,仿佛就这样走入了那个年代,那个有关上海的泛黄的记忆。
秋千,好像是古典世界的一个符号,带着浪漫主义色彩。那个坐在秋千上的女孩, 在舞台上,一个秋千,就营造了那个回忆里无比清新的场景,提示了故事发生的依靠的物质空间。秋千,象征着一种古典浪漫的感情,带着青涩的暧昧,和未知的憧憬。年华易老,江滨柳和云之凡之间的情书,好像是遥远却难以舍下的梦。江滨柳在病房中一次次回想着在上海那梦一样的回忆,可现实中的那个云之凡已老去。那个在秋千上摇曳的梦远去了。
但是,嬉闹之间,又含深意。在舞台上的那个井是一个神秘的符号。老陶一进入桃花源便遇见桃花源中的那对白衣夫妇。如果说能够把水井看成桃花源的象征,那么,寻访桃花源在另一种层面上讲,能够理解成人类想回归最原始那最初的自然状态。因为从现实来看,井象征着一种简单安然的世俗生活。不是当下杂乱无序的生活,那是我们想象中古代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平凡却幸福的日子。我们理想中的古典式日常生活,就应像白衣夫妇那样,悠然和睦,岁月静好,在风景如画的地方安然地生育后代。然而现实却是活在古代却毫无古典浪漫的老陶春花袁老板,或是苦苦守望着早已破灭的古典感情的江滨柳和云之凡,或许还有江太太。在本剧的高潮部分,即两部戏同台演出的段落,“井”成为了两个剧团现实场地的分隔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分隔物何尝不是联系物呢,联系着《暗恋》和《桃花源》,杯具和喜剧,戏剧和真实,古典和现代。这种强烈的比较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好像哪里缺了一块,就像那一块尴尬留白的空白幕布。剧中,“桃花源”导演“袁老板”发现布景上的一棵桃树只剩下一
片空白,而舞台上又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棵桃树时,十分恼火。他叫来美工小林。小林说,这叫“留白”。“留白?”导演立刻挠头。小林说:“这留白很有意境的啊!”“意境?”这两个本是表示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的最高境界的概念,可导演的疑问句式的“重读”,就表达了他对这样的古典概念的怀疑态度与不理解,或者是对现实的一种质疑。最后,百思不得其解的他,苦闷地大声喝问:“这棵桃� 缺了一块的幕布,仿佛在说这才是舞台上故事背后琐碎的混乱的生活。
但是,活在纠结不堪的现实里的人,心里总有一个梦。就像老陶误闯的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没有那纷纷落下的花瓣,或许我们想象不出那种场景。那随风飘落的花瓣,或是是生的梦幻,或是死的绚烂。在那漫天的飞舞中,谁会分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是欢乐还是忧伤。那个似痴似狂的陌生女人至始至终高一向喊着刘子骥这个代表着“寻找”的名字,发出了痴狂绝望的哀叹和呐喊。那个看似疯狂的女人,就像离开桃花源后再也回不去的老陶,就像苦苦守望着回忆的江滨柳,努力寻找着却再也见不到。寻寻觅觅之中,落花,迷了谁的眼,又落在谁的梦里。
在我看来,舞美的设计就像一件外衣,不是越华丽越美,而是恰如其分的细节美所展现出的优雅。《暗恋桃花源》的舞美设计,就如上方的文字所叙述的,每一个设计都凸显出匠心独具,贴合话剧所要呈现的物质空间和氛围。那么,话剧的语言就应是其灵魂,精雕细琢,从内散发出独特的美感。
相对《暗恋》,我觉得《桃花源》的语言更有爆发力,或者说给我更多更强烈的共鸣。在《桃花源》的第一幕中,老陶在喝不了酒,吃不了饼后发出的感慨。夸张的语言活灵活现的体现出老陶的性格特征和对生活境况的强烈不满。在老陶的生活中,家不再是幸福的港湾,酒不能喝,刀失去控制,饼硬的不能吃,甚至老婆偷人。按老陶的说法,这一切都已经不能再这样称呼了。这几句台词里体现出一种感觉,所有的一切仿佛失去了其本身存在的好处。生活,不像是生活,更像是一种只为存在而存在。另外,在“桃花源”第一幕,老陶家中三人的对话也很有有意思。刚开始,他们说了一些关于老陶打鱼的事儿。之后的对话中,大家都拒绝使用看来较为精确清晰的具体词语,代之以中国人口语中的“这个”、“那个”、“哪个”、“什么”等等。这种台词的模糊化在后面一幕老陶即将归来时春花和袁老板的对话中也有体现。从表面听起来这些话意思很模糊很迂回,但是我们都听的懂,都明白“那个”“这个”中所含的意思,不比具体的词语缺少任何一种应有的蕴含。这种模糊的语言,具有象征性,仿佛能无限扩大,到达另一种深度,比具体的语言更有张力和爆发力。最让我有震撼的是老陶说的“最当初,我们都不是什么。”这好像回到了对人类起源,
人类本质的询问。这句话有着巨大的力量,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还有一点是语言的白话化。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文字作为台词中的一部分,经过改写,加上了一些感叹词和生活化的字词,完全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息,脱离了一种文绉绉的感觉。在老陶回到武陵的那一幕时,在桃花源度过了一段纯真烂漫到近乎梦幻的时光的他回到武陵,发现原本如胶似漆,男欢女爱的春花与袁老板已陷入了现实的纠葛和相互的怨怼之中,并没有从此过着想象中幸福美满的快乐生活。从老陶,和春花与袁老板的对话中,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出这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很喜欢记得老陶说的一句:“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看起来好像走投无路了,但是,只要换一个观点,就能够立刻获得一个新的方向。”袁老板回应他的却是:“我觉得很累。”两种风格的台词,强烈的比较,令人哭笑不得之时,也发人深思。有一句话说话剧是语言的艺术。透过语言就能塑造了不一样的人物形象。语言真是奇妙。
记得其中有一句台词:人世间所有飘落的花瓣,每一片都是你的故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自我的故事。我们在努力生活,我们都在盲乱和期冀中寻找着永恒而真实的生活,谁会最终找到呢?